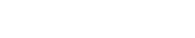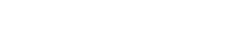(文章内容承接🔗《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相关规则对劳动法实务影响:格式条款(一)》。在之前选定的“样本案例”的基础上,我们补充了近期40个案例,一并作为本系列文章的“样本案例”。)
(四)关于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是否适用格式条款规制的探讨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格式条款规则处理规章制度规定相关争议的案例,如(2017)粤01民终23935号、(2024)京03民终18539号一审判决、(2024)粤0605民初11295号等。但要探究规章制度是否可以适用格式条款规则的问题,首先就要确定规章制度的性质,而关于规章制度的定性争议颇多,存在契约理论、法律规范理论、集体合意理论等十余种理论学说[1]。有学者曾总结:“劳动法学界较多认同授权法规学说”[2],但目前关于规章制度的性质并无定论。如果将规章制度视为合同(如“定型化契约”),则格式条款规制或有适用空间。
在一般民事争议中,确实存在非以合同形式出具的公告、告示等,被认定为视同格式条款。《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预先拟定的,对合同双方权利义务作出规定的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视同格式条款。”但在劳动用工情形下,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需经民主程序制定,并非完全由用人单位单方拟定,故而如认为规章制度并非合同性质,此类规章制度能否参照该规定视同格式条款,不无疑问。
总体而言,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应当经民主程序制定、公示程序公布,否则一般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用人单位对此已有稳定预期。并且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者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八十条,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损失赔偿,劳动行政部门也可采取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等措施。司法实践中裁判者也会考量规章制度规定内容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如果还要求用人单位注意格式条款规则,似乎苛责过重。且规章制度的性质并不明确,格式条款规则可能并不具备适用的条件。
(五)不属于格式条款的约定,不当然得到支持
在实践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为尽量避免格式条款规则的规制,在合同或协议中会考虑特别写明:本合同或协议并非格式文本,或相关条款不是格式条款。对此,《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合同条款符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仅以”“双方已经明确约定合同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为由主张该条款不是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其原因在于,为了维护市场秩序,格式条款规定属于不得排除适用的强制性规范[3],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识别,不受当事人之间的约定影响。因此双方约定争议条款并非格式条款,并不当然会得到裁判机构支持。
(六)关于是否属于格式条款的举证责任
普遍观点认为,对于格式条款,接受格式条款一方仅需就为重复使用、预先拟定、未经协商三要件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由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争议条款并非格式条款承担举证责任[4]。
但笔者认为,由前文关于“支付后再无争议条款”的分析可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之立“法”精神[5],支付后再无争议条款的格式条款争议,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不宜一概分配给用人单位对非格式条款的证明责任,反而应当由主张格式条款一方对条款未经协商进行举证。另外,前文所提及的合同“主要条款”,如果认为仍有适用格式条款规制之必要,也应由主张方对主要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进行举证。
在劳动争议司法实践中,法院也并未一概将格式条款的举证责任分配给用人单位一方。以“为了重复使用”这一要件为例,在(2022)甘01民终4642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上诉人所举证据不能证明案涉劳务派遣协议是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定的合同。又如,(2018)津01民终9622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劳动者表示理解《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的内容,主张该《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的内容为格式条款应为无效,且在签署该协议书时公司存在拒绝填写“单位要求不续约”的解除理由及威胁其不签字不为其办理社保手续等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
但为应对目前司法实践的不确定性,用人单位仍应尽量对容易产生格式条款相关争议的条款,做好实质经过协商、非重复提供等留痕工作,以应对可能的争议。不过,如前文所述,被识别为格式条款,并不一定会带来不利影响,因为格式条款规则所要控制的,是格式条款的不合理内容,而不是格式条款的形式[6]。因此,用人单位不必过于担心,增加过多成本。
三、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与效力规制及其在劳动争议中的适用与讨论
之所以将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效力规制在本章中一并进行分析和介绍,是因为两者在条文表述上存在相似之处,同时,二者又与《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即劳动关系中的效力规制,也存在相似之处。因此如何界定三者的内涵和关系,直接影响格式条款在劳动争议中的适用意义、适用规则,有必要将三者一并讨论。
(一)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制
如前所述,格式条款的订入规则是劳动实务中应当关注的重点规则。该规则规定,格式条款提供方如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对特定格式条款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经接受格式条款一方进行主张,该格式条款不得成为合同内容。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条中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已经履行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说明义务。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其已经尽到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1.受订入规则规制的条款范围
《民法典》中规定受订入规则影响的格式条款为,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第四百九十六条明确列举了免除或者减轻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条款属于该类条款。而在《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中,受订入规则影响的格式条款为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同时相较《民法典》规定,额外列举了排除或者限制对方权利的条款,也可能属于此类“异常条款”。
根据最高院的解释,之所以《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中受订入规则规制的条款范围与《民法典》表述不同,是因为合同中可能有很多“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如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等涉及权利义务关系实质性内容的条款”[7],而如果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这些条款都要履行提示义务,可能导致“满页飘红”,使提示流于形式。因此,应将“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限制在“异常条款”[8]。
所谓“异常条款”(Surprising Clause),学理上认为,“是指订立格式合同时,依照交易的正常情形,显然不是相对人能够预见的格式条款”[9]。而对于如何判定“相对人能够预见”,一般认为采取社会一般人标准,即“从具体交易的性质、目的、形式逻辑以及生活常识和管理等因素来看,这种条款存在于格式合同中是社会一般人不可能普遍预见和认同的”[10]。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异常条款”,其内涵是否与前述“异常条款”内涵一致,不无疑问。其效力也与一些学者建议借鉴的国外“异常条款”效力并不相同[11],该“异常条款”并非一概不订入合同,而是限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如果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的,经对方主张,不成为合同内容;若该异常条款达到《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的,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程度时,则归于无效[12]。而对于判别“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标准,一般认为需依据具体案件的情况及合同的类型特点来判别[13],有学者也认为可以借助和参照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列举性规定来进行判断[14]。
在劳动争议中,如何界定此类“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异常条款”,尚缺乏统一指导,相关案例也非常少。在(2021)闽0902民初3786号判决书及类案判决书中(判决时《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尚未发布),就涉案的保密和竞业限制协议,法院认为:公司主张劳动者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合同条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为依据,“对于权利义务的配置未明显偏离于法律文本的安排,可为社会一般人所预见”,且劳动者作为硕士生“其专业智识和工作经验均高于常人”,“故此不属于超出对方当事人始料所及范围的异常条款,提请注意并非必要”。该案中,法院是依据涉案条款内容未超出法律规定范围,认定了该条款是可为社会一般人所预见的条款,并结合了当事人的具体认知和经验状态,最终认定了涉案条款并不属于异常条款。
从样本案例来看,在《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则下,法院认定用人单位需要履行提示说明义务的格式条款主要包括:竞业限制协议条款、离职文件免责条款、工资定期异议条款、协商解除协议支付后再无争议条款、调岗条款等。
2.提供格式条款方的提示说明义务
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方应当履行的义务为: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或按照对方的要求对条款予以说明,即提示或说明义务。《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条则对提示或说明义务的内涵予以了明确:采用了通常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可认定为履行了提示义务;一方按照对方的要求,就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对方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可认定为履行了说明义务。在实务中,一般对于争议条款进行了加粗、下划线、显著不同颜色或字体等特殊标注,由劳动者进行了手写,或有证据对争议条款内涵进行了说明,可被认定为履行了提示或说明义务。
此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十条第三款对于电子合同的提示说明义务进行了特别规定:“对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仅以采取了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为由主张其已经履行提示义务或者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对于用人单位而言,采用“电子签”方式与劳动者订立劳动相关合同的,仍需按前述方式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而不能仅以设置勾选、弹窗等方式规避该义务。
3.劳动争议中格式条款订入规则适用的影响
《民法典》在制定格式条款订入规则时,充分考虑了绝对无效规则给条款接收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以及原司法解释规定的对格式条款的可撤销权仅能在一年诉讼时效内行使的不利影响,最终采纳了将该制度归属于合同订立范畴,而非效力评价层面的规则[15]。经相对方主张不成为合同内容的条款,应当不会涉及条款的效力问题,实际上无需再根据格式条款效力规制加以判断。但从样本案例来看,很多判决既论述了争议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又论述了该条款无效。虽然这种判决逻辑对于当事人争议的权利义务不会产生额外的影响,但实际也提示了用人单位,在制定相关条款时首先要考虑该条款是否会因排除或加重劳动者权利、免除或减轻用人单位义务等原因而被认定无效。无效的条款,即使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也不能作为双方处理争议的依据。
目前劳动司法实践对于格式条款能否适用的不确定性,使得用人单位唯一有效的应对之法,就是针对格式条款争议频发的相关条款,或双方相较一般用工确有特殊安排的条款,依照前述方法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并做好留痕,以尽量避免出现格式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相关争议。
注释:
[1]沈建峰:《劳动法的教义学建构研究》,法律出版社2024年版,第252-253页。
[2]林嘉:《劳动法的原理、体系与问题》,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26-227页。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127页。
[4]同前注,第131页。
[5]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行的司法解释具有类似于制定法的权威性。易军:《论合同违反强制性规定无效的判断标准——以〈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16条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24年第1期,第7页。
[6]原文为“我们所要控制的是免责条款的不合理内容,而不是免责条款的形式”。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8版,第919页。
[7]如认为核心给付条款或主要条款不应适用格式条款规则审查,此类“涉及权利义务关系实质性内容的条款”,应当不涉及格式条款规制,也就不涉及说明提示义务。不过特别法有规定的,应当从其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8]同前注3,第18页。
[9]张建军:《“异常条款”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5期,第136页。不过目前国内关于异常条款的专门著述并不丰富。
[10]同前注。
[11]参见前注9;参见韩世远:《民法典合同编一般规定与合同订立的立法问题》,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3期,第28页;
[12]参见王利明、朱虎主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释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95页。孟强:《合同格式条款效力的法律控制——以〈民法典〉合同编及其司法解释为中心》,载《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50页。
[13]赵童:《论格式条款的订入控制与效力控制——以〈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9条、第10条为中心》,载《法学杂志》2024年第6期,第60页。
[14]孟强:《合同格式条款效力的法律控制——以〈民法典〉合同编及其司法解释为中心》,载《广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第251页。
[15]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86页。
- 相关领域
- 劳动人事